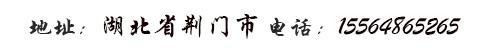巴拉特middot戈埃尔海洋统治法律
|
作者简介 作者:巴拉特·戈埃尔(BharattGoel),印度古吉拉特邦国立法学院法学学士在读。 翻译:陈曦笛,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硕士生。 校对:张洁芳,宁波大学法学院本科生。 ■■■■ 声明 本文原载于TheblogoftheNorwegianCentrefortheLawoftheSea,题目是“TheSeaDominatestheLaw:RiseinSeaLevelasaGrotianMoment”。本文谨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译者和平台立场。 全球海平面上升已经展现出对国际法的挑战,并打开了法律问题的潘多拉魔盒,促使国际法委员会将之纳入长期工作计划。该问题涉及国家海洋管辖权和主权,特别是对低地势沿海和岛屿国而言。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条(以下简称《公约》或《海洋法公约》)规定,一国之各类海域依沿岸低潮线(即基线)确定。进一步看,根据《公约》第47条第(1)款,最外缘各岛和各干礁的最外缘各点被用作绘制群岛国家基线的坐标或基点。在这些基准和基点的帮助下,一国的所有其他海洋权益也得以划定。 陆地统治海洋 这一原则在国际法院审理的北海大陆架案件中得到承认,其明确指出“陆地是一国可行使领土延伸至海洋的权力的合法来源”(第96段)。正是基于这种联系,领土或主权纠纷必须在处理海洋争端前得到解决(第32页)。依据这一原则,基线也被认为是流动或非静态的(第31页)。通过取得新领土或建造人工岛屿得以认为延长的基线,扩大了国家的海洋管辖权。同理,由于淹没或基点消失而造成的领域损失则会引发(海洋管辖权)收缩。此外,《公约》第条编纂了一项习惯国际法(第段),规定所有自然岛屿都源于海洋区域。且根据其后的条款,无法维持人类一定水平的居住或经济生活的岩礁,不产生任何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权利)。因此,根据上述原则,海平面上升和领土淹没可能对海洋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对以岛屿和岩石为基点的群岛国。当前国际成文法似乎没有为此问题提供任何适当的解决办法。 海洋统治陆地 当前两种新法律(delegeferenda)解决方案已被提出。其一,冻结基线以维持现有权利。其二,沿海国可以在不冻结基线的情况下,选择保有其海洋权利的外部界限。为此,相关国家必须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交存,显示基线和边界的地理坐标(《公约》第16(2)条、75(2)条、47(9)条)和海洋区域边界(《公约》第75(1)条)的海图或清单,并且适当地对其出版和宣传(《公约》第16(2)、75(2)、49(9)条)。两种情况下,基线的改变和基点的消失,但都不会减损海洋管辖权主张。然而,这两种解决方案都被认为违反了“陆地主宰海洋”的原则,并试图地理环境已经与之不符的先决条件下,固化一国的权利主张。不过,有争议的是,上述原则正受到“海洋主宰陆地”原则的挑战,其(海洋主宰陆地原则)正在以习惯国际法的方式被逐渐固定下来。 国际习惯法公理 国家实践与法律确信国家实践可以从国家的立法性和行政性行为中得到体现(“习惯法国际的识别结论草案”(以下简称“识别结论”)第6条第2段)。各国政府发表的法律意见及其在国际和政府间会议上的行为则可以证明法律确信(识别结论第10条第2段)。越来越多的沿海国赞同在不考虑海平面的情况下,永久建立基线的想法。波利尼西亚领导人小组(PolynesianLeadersGroup)在年签署了《塔普塔普阿铁阿宣言》(TaputapuateaDeclaration),呼吁永久冻结各自的基线。同样,太平洋岛屿论坛也敦促其成员国划定其海域,并完成既定的证明、公布和宣传要求。《瑙鲁协定》(NauruAgreement)缔约国也同意永久延续目前基线。此外,这些国家也在颁布国内法,单方面地宣布其海洋基线和边界。同时,海洋法庭选择了严重偏离“陆地主宰海洋”原则,也削弱了其重要性。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孟加拉—缅甸争端中援引公平解决的考量,无视孟加拉国管理的、具有永久居民的圣马丁岛(St.Martin’sIsland),认定其与调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等距线无关(第段)。南海仲裁案最恰当地反映了对“陆地主宰海洋”原则的背离(第段)。法庭着眼于地理特征,并考虑建立专属经济区制度的总体目标和宗旨——禁止和限制人为制造的权利,以确定这些特征是否可以产生作为岩礁或岛屿的海洋权利,而不是以地理区域的本质作为法庭的裁决基础。因此,法庭的做法含蓄地支持了“海洋主宰法律”的观点。 特别受影响国家理论诚然,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都源自部分沿海国。“海洋主宰陆地”原则能否被确定为国际习惯法规范?当适用特别受影响国家理论时,也许可以。包括利益受到特别影响国家在内,广泛而有代表性的参与,足以形成习惯国际法(第73段)。然而,特别是对已经就国家实践的普遍性和所赋权重问题,辩论过该原则有效性的国际法委员会而言,其有一个“阿喀琉斯之踵”(第95页)。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毫无疑问,将对沿海国产生更严重的不利影响,因为它们将经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海平面上升(第页)。沿海国面临着被剥夺领土、人民流离失所和完全丧失国家地位的威胁。Shaw认为,受该事项特别影响的国家可以单独产生一种习惯规范,而无须得到其他不受特殊影响国家的支持(第页)。另者,特别受影响国家,特别是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可能会形成一种区域习惯(识别结论第16条)。沿海国的实践和海洋法庭目前的裁决一致表明,支持因海平面上升而修正海洋划界原则。无论如何,特别受影响国家对“陆地主宰海洋”原则的强烈异议,将不会允许它继续长享以往的地位,尽管其得到了来自北半球国家的政治支持(第页)。 “格劳秀斯时刻”的海平面上升 特别受影响国家理论也免除了暂时的时间要求,即实践应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形成习惯规范(第73段)。迈克尔·沙尔夫(MichaelScharf)创造了这个词,指向国际秩序中的根本性变化引致国际习惯法的快速形成(第页)。海平面上升可以被认为是,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变化导致“海洋主宰着陆地”原则快速被提升为海洋划界新国际习惯法规范的最新实例,虽然(这种变化)也并非一蹴而就。 以上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本推文图片转自百度图片,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法眼看南海”由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徐奇博士及其团队运营,旨在介绍和分析与国际法和南海问题有关的信息动态和名家学说 联系邮箱:xuqi jnu.edu.cn图文编辑:吕竞一大连海事大学研究生 审校:徐奇暨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apitia.com/pptly/8204.html
- 上一篇文章: 杭州超值五星大酒店来啦更有长乔极地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