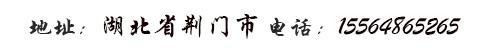追求金钱自由还是精神自由保罗middo
|
阅读本文时,建议您点开音乐,边听边看感受更佳。 CHAPTER01记忆中的你离开梵高后,高更返回布列塔尼。他先在阿望桥呆了一段时间,然后来到一个名叫布多的小渔村。高更在布多收了一群忠实的弟子。当夜幕降临时,艺术家们停止了工作。他们抽烟痛饮,喧闹地弹奏吉他和钢琴,激烈地讨论着彼此的作品。临睡前,他们还会在餐厅里下跳棋。在布多时光的尾声,高更创作了《橄榄园中的基督》。高更作品《橄榄园中的基督》 人们能在《福音书》上找到其所描绘的场景。整幅画中充满了高更的个人共鸣。在阿尔勒与梵高同住时,梵高经常谈论宗教绘画的价值。在大多数情况下,高更这个法国人对这位荷兰同行的话都不屑一顾。这幅画可以说是献给梵高这位朋友的迟来的、充满歉意的作品。《橄榄园中的基督》局部画中基督的红色头发和胡子正是对应了高更心中梵高的形象。高更曾给梵高写过一封信,附带了这幅画的草图。梵高一如既往地坚信画家应该准确地观察世界,而不是描绘自己的想象和记忆。梵高苛责高更画中的橄榄树,认为它们的样子完全不对。CHAPTER02前往塔希提岛年,高更卖了一大批画。他终于可以放飞梦想,航行到南太平洋去。朋友们大摆宴席为他饯行,梅泰反应却很平淡。高更与妻子梅泰 (注意高更的眼神) 从马赛到的塔希提岛的旅程历时两个月。虽然买的是二等舱,但当过水手的高更很快和船员们打成一片。大多时候,他都在船尾比较舒适的舱位度过。自欧洲人第一次登陆塔希提岛,他们就把那里视为天堂。在无尽的海上航行了这么长的时间,水手们立刻爱上了那里,爱上了岛上温润的气候和丰饶的蔬果。他们的船在晚上到达,在黑色天空的背景中,高更看到地平线上升起的锯齿状的群山轮廓。这里仿佛大洪水退去后第一片干燥的土地,是孤独的家庭坚守的避难所。CHAPTER03失落的天堂当他在塔希提岛的首府帕皮提离船登案,高更感到非常失望。这里不再是伊甸园,倒像典型的法国殖民地:到处是新建的欧式建筑,殖民官僚把自己那套规章制度强加于当地居民,新教与天主教的传教士们极力说服塔希提人放弃他们的原始信仰转投基督教。高更哀叹道:塔希提正“逐渐变成法国的一部分,古老的生活将日渐消亡”。高更作品《午休》他原本希望看到野蛮人,却发现“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正通过殖民渗透逐渐侵入当地文化,到处都是不伦不类的拙劣模仿,包括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声音语调和各种文明的谬论”。他沮丧地在日记中夹入了一张照片:塔希提国王竟然穿着欧洲人的军装。塔希提人觉得这个穿着奇装异服、留着长发的艺术家是个有趣的人。当地殖民政府却并不这么看:他们怀疑高更是法国政府派来监视他们的。CHAPTER04野蛮的痕迹在失望之余高更依然相信,虽然近期采用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服饰,但在这些外表之下塔希提人依然保持着他们真正的本性——能从他们眼中深切地看到一团火,高更称其为动物本质的优雅和激情。他被塔希提女人们的美丽优雅深深吸引,同时在他的想象中,她们又具有食人的本性,这点让他感到恐惧。高更作品《ThemonthofMaria》 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一段可能是他臆想出的故事:他在帕皮提遇到了塔希提岛的公主。当公主第一次踏进他的房间,他感觉她像一只猛兽,她“吃人的”爪子似乎随时准备撕裂食物。一起喝了一瓶苦艾酒之后,她的态度有所改变:现在能看到他的美了。高更作品《香蕉》高更对于塔希提女人的看法是典型的欧洲人的眼光,他们都错误地相信在西方人中流传了一个多世纪的关于波利尼西亚的神话故事,其中有好有坏。CHAPTER05深入丛林高更和其他欧洲旅行者的不同在于,他想尽可能地贴近塔希提岛和当地文化。他强烈地想隐藏起自己的文明特性,希望有朝一日能如愿以偿地成为一个野蛮人。为了这个目标,他离开帕皮提,去寻找一处纯净而未开化的原始地。他在塔希提岛西南岸的马泰亚村租了一栋木屋。高更作品《白马》从他的小木屋望出去,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海面,还有碧蓝的泻湖和水底的珊瑚礁。向东望去,可以看到小岛远处的边缘,以及罗牛山的悬崖峭壁。小屋周围满是椰子树、面包树和高大的蕨类植物。高更经常坐着观看当地男人们捕鱼,而女人们则在岸边收拾渔网。高更作品《海滩上骑马的人》虽然很开心,但他很快意识到生活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离开这里之前,他曾写信给丹麦的艺术家朋友威尔姆森说:“在从不见寒冬的天空之下,这片极其富饶的土地上,塔希提人所要做的只是俯身拾起食物,因此,他们从不需要工作。”而实际上,高更发现自己难以养活自己。他不会捕鱼,种植农作物则是当地农民的营生。幸运的是,当地村民怜悯他,赠予他一些食物。高更作品《法国花》高更写信告诉梅泰,塔希提人尽管被称为“野蛮人”,但他们的善良好客让他们远比欧洲人更文明。CHAPTER06万福玛利亚在《万福玛利亚》中,高更精心地把塔希提岛描绘成了天堂。高更作品《万福玛利亚》 在南方蔚蓝色天空下,林木葱茏繁茂,前景中有令人垂涎的芒果和面包果。这一派伊甸园景象的中央,是一对理想化的母子,身后还有两个女子。母亲高贵的面庞和强壮的臂膀非常符合高更所形容的岛上居民的自然美,与欧洲人相比,他们两性间的差异要小得多。他把波利尼西亚女性富有活力的身体与法国女人被紧身束衣弄得苍白单薄的身体作对比。裹裙——一种波利尼西亚女人穿着的传统长袍——和水果、蔬菜靓丽的色彩表现了高更眼中的塔希提岛:一个奢华而温暖的地方。《万福玛利亚》局部 为了表示他已然与塔希提文化融为一体,高更在画面上用塔希提语写下了标题。标题翻译过来即“万福玛利亚”或“伟大的圣母玛利亚”,表示这幅画不只是一幅诗情小岛的风景画。画中的母亲和儿子让人想起欧洲图像中的圣母和耶稣,仔细观看我们能发现,两个女人身边的灌木丛中还隐藏着一个天使。灌木丛中,穿粉红色衣服的天使《万福玛利亚》局部高更似乎在暗示,塔希提岛有着《圣经》人物那样的纯洁性,而这正是欧洲人已经丧失的东西。又或者他意识到,即便是马泰亚的当地人也已经被基督教传教士改变了。CHAPTER07高更的女人们高更着迷于塔希提岛的风景,也对当地女人痴迷。在塔希提岛的这段日子里,他竟然很少想念梅泰。来到帕皮提后,他遇到的第一个爱人叫提提。但他很快失望地发现,提提只有一半的塔希提血统——他父亲是英国人。而且,她被首府的生活宠坏了,过于热衷西方的服饰和生活习惯。他动身去马泰亚时,就把提提抛弃了,因为她不符合他心目中那种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理想的波利尼西亚人的形象。在马泰亚,高更费了很大功夫劝说村子里的一个年轻姑娘给他当模特。起初她很抗拒:这一点也不奇怪,她很警惕这个奇怪的外国人。但她最终还是同意了,高更于是赶紧给她画像,以免她临时变卦。高更作品《两个塔希提女人》 高更笔下的她和其他的塔希提人一样:照欧洲的标准算不上漂亮,但还是很美。高更把她的嘴画成一条简单流动的线,所有快乐和痛苦都融入其中。在高更的小屋里,年轻姑娘看到挂在墙上的马奈名作《奥林匹亚》的照片。她问:“这是你妻子?”高更故意逗笑说是。年轻姑娘说她很漂亮。高更立刻想起,马奈这幅画曾被大多数法国批评家称作丑陋不堪的作品。高更认为,年轻姑娘的反应证明了,塔希提人对于真正美的事物有一种发自本能的欣赏能力,而这恰是欧洲人已经丧失了的。CHAPTER08泰阿曼娜尽管痴迷于马泰亚的自然之美,高更发现因为强烈的孤独感,他还是无法工作。于是他开始寻找新的爱人。他受邀去某个小村子吃饭,于是便骑着一匹借来的马沿着海岸去了那里。一个女人把他的女儿泰阿曼娜介绍给他,高更欣然接受了。泰阿曼娜极其年轻,只有13或14岁。高更在日记中试图对他们的关系作出合理解释,便说这是当地习俗。高更在给梅泰的信中暗示了他和泰阿曼娜的关系,而梅泰怎么想,则无人知晓。高更作品《你何时结婚?》 高更被泰阿曼娜迷住了,她常常沉默不语,高更把这视为她深奥内在智慧的象征。她的沉默似乎在说,她对这个进入她家庭的法国画家没什么话可说,但高更则在年轻伴侣身上看到了神秘感。高更凝视着她黑色的眼睛,发现自己无法读懂她的想法,他想象自己在其中发现了动物的纯真和野蛮人的忧郁。泰阿曼娜的左脚居然有7个脚趾,这更强化了她身上异国情调的差异性所蕴含的神奇魅力。泰阿曼娜陪伴在高更身边时,他感觉自己变成了塔希提文化的一份子,“文明正在一点一点离我远去,我开始学会简单地思考……自由地生活,享受动物和人类的欢愉。”最后,当泰阿曼娜静静地坐在他身边时,他终于可以连续数小时不停地作画。高更完全被塔希提夜晚的静谧迷住了。“塔希提岛宁静的夜晚是世上最奇妙的体验,”他写信对梅泰说,“只有这里才有如此的宁静,没什么会打扰人的清心,甚至连鸟鸣都没有。”随时随地都有干枯的落叶掉落,但也没有任何声响——它更像是轻轻地抚触着灵魂。岛上居民经常在夜间行走,但同样毫无声息,几乎听不到脚步声。高更作品《塔希提的牧歌》高更相信,只有在黑暗的夜色中,塔希提岛才能显示出其最深沉的神秘。在日记中,他记录下想象中在夜色里与灵魂和南太平洋的神性遭遇的场景。在阿维伊山,高更希望能见到磷光,根据当地信仰,当夜幕降临,祖先的灵魂就会出现在人们面前。在漆黑的夜晚,高更看见在他脑袋周围有一种粉状的光亮,但他自己写道,这其实只是他生火用的干木头里真菌释放出的光亮。高更作品《敬神节》 高更被塔希提人关于月亮和星星的起源的神话深深迷住了。欧洲人所谓的双子星座是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塔希提人认为是双王,是天空之神和妻子的两个儿子。高更说,他是从年轻爱人泰阿曼娜那里知道这些塔希提神话传说的,他们躺在床上时,她一点点讲给他听。实际上,高更是从一本荷兰星象学家的书里读到的。泰阿曼娜不太可能知道这些古老的故事。CHAPTER09死亡的幽灵在注视某一天,高更去一个小镇找寻乡间小屋。晚上回到家,他突然在黑暗中感到一阵恐惧而颤抖,他划亮了一根火柴,看见泰阿曼娜(他在日记中称她为泰胡拉)惊恐地躺在床上。他这样描述这个场景:“泰胡拉,面朝下一动不动裸身平躺在床上,眼睛中带着极端的恐惧。她看着我,似乎没认出我。我也怔住了,呆呆地站了一会儿。泰胡拉的恐惧似乎蔓延到了我身上。我仿佛从她闪烁的眼中看到了某种灵光。我从没见过她如此美丽,一种让人震撼的美……我一动都不敢动,生怕些许的动作都会加剧这个孩子的惊恐。我怎么才能知道,在那一刻在她眼中我是什么样子?难道说她把我惊恐的面孔当成了什么妖魔鬼怪,比如传说中会在失眠之夜出现的妖怪图帕珀(Tupapau,波利尼西亚神话中的妖怪)?”高更作品《死亡的幽灵在注视》 女孩的恐惧似乎让高更产生了强烈的兴奋感,他于是创作了这幅《死亡的幽灵在注视》。他怀着强烈的快感来描绘她年轻又柔弱的身体,把它突显在画面中央。同时,他也试图去体会女孩的感情,想象女孩会如何看待他。高更想让我们不要把他视为一个置身事外的观看者,而应该是融入塔希提人经验之中的当事人。他似乎像泰阿曼娜一样能感觉到图帕珀的存在,所以他把它画在雕花床柱的一边。画面上没有刻意画远景,最大限度地缩短了艺术家和他所描绘的景象之间的距离。高更采用单纯的形式和色彩似乎在证明,他抛弃了文明化的方式,变成了像泰阿曼娜那样的“原始人”。死亡的幽灵在注视(局部) 尽管基督教传教士摧毁了塔希提岛绝大多数宗教系统,但人们对于图帕珀的畏惧却始终存在。高更知道一些波利尼西亚神话传说,但事实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泰阿曼娜告诉他的,而是他从一本书中读到的。但这一次,是高更告诉他年轻的爱人关于夜间幽灵的故事。为了捕捉泰阿曼娜等候在黑暗中时产生的恐惧感,高更采用了阴暗的色调。“和声,”他写道,“是多么阴郁而令人恐惧,它在眼中萦绕就像是葬礼上的丧钟。”他在背景上画了一些亮光,代表了自己曾在塔希提岛中心的圣山——阿维伊山间看到的那种磷光。死亡的幽灵在注视(局部) 高更急切渴望融入塔希提人的生活,但他始终记得自己作品真正的观众不是这些波利尼西亚人,而是欧洲人。他把《死亡的幽灵在注视》连同其他作品一起寄往巴黎展出。他还安排作品在哥本哈根展出。尽管他和梅泰的婚姻是失败的,但梅泰仍然尽其所能为他筹措资金,组织展览。或许是害怕梅泰及其家人把作品视为他不忠的证据,高更杜撰了另一段与日记记载截然不同的故事。他宣称,这不是一幅不雅的私密写照,而只是一项裸体研究,是某种生活的象征,其中包含了少女,以及图帕珀代表的死神。CHAPTER10成为野蛮人高更把塔希提人形容为野蛮人其实是对他们的恭维。他把自己也看作野蛮人,因为他有秘鲁血统。他的希望是变成更加纯粹的野蛮人,抛弃原有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高更作品《DerEinbaum》在马泰亚村时他交了个朋友,一个叫托泰法的年轻人。高更在日记中记录了某一天,他把锤子、凿子和一块木头交到托泰法手里,并试图教他如何雕刻。托泰法把工具还给高更并对他说,艺术家是与众不同的一种人,他相信高更能够创造艺术,他是“对于别人有用的人”。高更被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这些话跟梅泰惯用的指责截然不同,梅泰只会指责高更过于自私,说他应该照顾家庭,而不是徒劳地浪费时间。高更写道,托泰法的话是野蛮人或者孩子才会说的话,只有这些人才会从本质上理解艺术的真正价值。他认为欧洲的成年人太看重所谓的现实性问题以及金钱。高更需要更多的木头用来雕刻,托泰法带他艰苦跋涉进入深山,寻找一种铁树。高更作品《举着斧头的男人》(已打码)当高更畅快地砍树时,他感觉自己真正变成了一个野蛮人:“我狂暴地砍伐着,双手被磨破而沾满了鲜血,我纵情于这种残暴的愉悦之中……我残存的那点儿文明人的印记被彻底消除了。我重新获得了平静,从这一刻起,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一个毛利人。”CHAPTER11一种消失的文明高更意识到自从欧洲人踏足塔希提岛之后,这里已经改变了太多,他想见见这里曾经的样子。在日记中,他描绘了一次探寻远处村落的旅途,在那里他仿佛看到了往日重现:“尽管离得很远,我依然清晰地看到他们的神像出现在我面前,之后就消失了。特别是月亮女神辛娜的神像。”他甚至想象听到了过去的声音:“人们围着她,参照古代的仪式翩翩起舞,唯沃(vivo,一种波利尼西亚芦笛)的曲调随着光线的明暗变化从轻松欢快变为低沉忧伤。”高更作品《你为何生气》 (已打码) 高更经常把塔希提岛想象成欢乐和忧伤两种模样:究竟是一个物产丰富、幸福快乐的岛屿,一个热带天堂,还是一个大洋尽头与世隔绝的荒僻之地,一个当地文化正在消亡、古老的宗教遗迹日渐倾颓的地方?因为大多数古代雕像都消失了,于是高更在画中描绘了许多非西方的内容——佛教的、日本的、古埃及的——以此臆造出塔希提宗教艺术当年可能的模样。CHAPTER12塔希提的灵魂世界高更不仅幻想自己看到了消失已久的古代雕像,还声称自己看到了塔希提岛的灵魂。在另一次深入岛屿腹地的探险中,他说自己在路的拐角遇到了一个年轻女子,当时她正把水淋在胸口。当发现高更后,她立刻消失在水中,变成了一条鳗鱼。高更作品《Inthewaves》这一描述令人生疑,因为人们发现高更把这次遭遇神秘物的经历画在画上,但这个形象其实来自他买的一张法国照片。照片上,一个萨摩亚男孩正在泉水边饮水。在塔希提岛住了将近2年后,高更的钱用完了。他担心巴黎的艺术世界快要把他忘记了,于是决定返回法国。他希望重新建起他在艺术界的声望,并寻找肯买他作品的买主。高更笔下的泰阿曼娜高更在日记中写道,当他告诉泰阿曼娜这一决定后,她哭了好几个晚上。当他的船离开时,她静静地坐在码头,虽然悲伤但很平静。高更的日记并不可信。他的描述很像皮埃尔·洛蒂的小说《洛蒂的婚姻》的结尾,这是一部高更熟读过的关于塔希提岛的浪漫小说。CHAPTER13回到巴黎年夏末,高更回到巴黎与老朋友再度聚首。经历了塔希提的静谧后,他倒是很享受咖啡馆和工作室的那些嬉闹。他经常邀请别人去他的画室,给他们讲在南太平洋时的故事,或给他们弹奏脚踏风琴。弹奏脚踏风琴的高更, 高更发现很难重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重要的艺术家。他在塔希提岛的两年里,其他艺术家已经吸引了批评家的眼球。尽管他在一个重要的画廊和他的画室都举办了展览,他特意创作了一组(10幅)木刻版画,同时展出的还有已经出版的塔希提日记。他原本指望日记有助于给批评家们解释这些塔希提绘画,但遗憾的是这些文本没能及时完成。高更作品《诺阿诺阿(芬芳)》 不过,这些木刻有效地记录了他的兴趣。它们被刻得相当粗犷,为的就是表现艺术家的野性本质。扉页画的是一群人围着一棵树。两个较小的人物表现的是塔希提岛的亚当和夏娃,它们在知识之树下休憩;较大的人物则是塔希提岛的居民。高更想要控诉的是,欧洲人到来之后,塔希提岛的居民丧失了它们的天真本性。如今,伊甸园被破坏了,塔希提岛的人们都被迫劳动。高更在巴黎只卖出了很少的几张画,他没有吸引多少评论,只有一些朋友写了些评论文章。失望于自己没能重整往日雄风,同时也迫于经济问题,他重返布列塔尼,希望能复兴阿望桥画派。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个叫安娜的年轻女子,高更说她是爪哇人,但她其实更像是斯里兰卡人。糟糕的是,高更发现布列塔尼并不比巴黎好到哪里去。他无法像以前那样呼朋引伴,成为弟子们崇拜的中心人物,往日的老朋友们早已经各奔东西,或者已经成名成家了,比如贝尔纳。高更疯狂地认为贝尔纳剽窃了他的想法,然后跟批评家们说是自己的艺术创造。高更的怀疑或许有些根据:贝尔纳一直鼓吹自己才是阿望桥真正的革新者,而非高更。高更自画像朋友圈的分崩离析让高更心灰意懒,他在布列塔尼找不到心灵的安慰。他发现无法实现自己长久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建立一种与本地居民之间真正的亲近感。这些人有时甚至对陌生的艺术家表现出极大的敌意,孔卡诺小镇曾以捕鱼船队和沙丁鱼工厂而闻名,这些至今人们还能在码头附近看到。高更曾经在那里被一群布列塔尼水手殴打,事件的缘起可能是他们侮辱安娜和她的宠物猴子。在打斗中,高更的脚踝受了重伤,以至于卧床了4个月。更糟糕的是,在他卧床期间,安娜竟然偷光了他画室中所有值钱的东西返回巴黎。高更作品《市场》 这是最后一根稻草。高更此次返回法国以耻辱告终。他既无盟友也无买主,一事无成。他确信自己在欧洲毫无前途,命中注定还要返回波利尼西亚。年夏,他最后一次离开了祖国。CHAPTER14重返塔希提岛高更带着重获新生般的乐观重返塔希提岛,在距离帕皮提几英里的小岛普纳奥亚安顿下来。他建造了一所木屋,里面有几间卧室和一个阳光照耀的画室。高更在塔希提岛的木屋 约 他发现此时的泰阿曼娜已经嫁人了。很快,他又找了另一个羞涩的女孩,只有14岁的帕胡拉。她后来为高更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女孩,出生几天就不幸夭折。第二个是男孩,名叫爱弥尔,非常长寿,80多岁还在给游客讲述他父亲在塔希提岛的故事。他和帕胡拉的第一个孩子降生时,高更绘制了这幅《降生》。高更作品《降生》他把基督降生的《圣经》故事搬到了波利尼西亚,帕胡拉就像是圣母玛利亚,新生儿就像是基督,另外还添加了两个塔希提女子。此画的构图与《死亡的幽灵在注视》前后呼应,但早期那种阴暗的调子已转变成新生活的欢乐。高更用基督降生的图像模式来描绘自己孩子的降生,似乎暗示了身为艺术家的自己就像上帝一样有着创造力。CHAPTER15贫病交加离开法国前不久,高更从妓女身上染上了梅毒。抗生素发明之前,人们根本没法有效治愈这种破坏力极强的恶疾,它一点点地摧毁着高更的身体。他腿上开始出现溃疡,尤其是脚踝病得最重,疼痛难忍,因为自从孔卡诺小镇的那次受伤后,脚踝就一直没能痊愈。有一段时间,他甚至病得卧床不起。更糟糕的是,他身上的钱也很快耗尽。为了活命,他甚至一度为自己憎恨的殖民政府工作。这些困苦,连同彻底的孤独感(没有一个老朋友给他写信),把他带到了绝望的边缘。高更作品《BildnisVaiite》局部年,传来了更坏的消息,久未通信的梅泰来信说,他最疼爱的女儿阿琳因肺炎病故。高更的阴郁情绪体现在这幅《各各他附近的自画像》中。高更作品《各各他附近的自画像》 他又一次把自己比作基督:各各他是基督受难的地方,耶稣在各各他山上被送上了十字架。而此时的高更已然情绪低落、麻木不觉了。与之前的自画像相比,如今的他显然形容枯槁、毫无激情。画面上也不再有之前的那种鲜艳明亮的色彩。他身后是各各他山阴暗的山坡,仿佛预示着这一次他注定无法逃脱自己的宿命。贫病交加之中,高更意识到自己最终的受难之日已不远了。CHAPTER16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将到哪里去?经历了几次心脏病以及梅毒造成的身体损伤后,年底,高更试图走进深山,以服食砒霜的方式自杀。他设想在森林中自杀,在参天古树和塔希提岛静谧的怀抱中孤独地死去。但他的几次尝试都失败了,隔天早晨他又把自己拽回了画室。他给法国的一个画家朋友丹尼尔·德·蒙弗雷写信,讲述了自杀失败的经过,还提到他不久前开始创作的一幅画,一幅“遗嘱”式的作品。它就是那副将近有4米长的大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将到哪里去?》。高更作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将到哪里去?》 令人吃惊的是,高更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画完了这幅画。他抓紧时间疯狂地把想法都画在画布上,因为他相信死亡即将降临。“临死之前,我把所有能量都注入此画中,这是一种在如此糟糕的环境中的痛苦激情,我眼前的景象是如此清晰,仿佛所有匆匆逝去的事物和生活都一一再现。”此画探讨的是人类的神秘主义,背景则是塔希提岛的全景。高更采用了一种典型的象征主义手法,设计了一幅极为复杂的图像,其中蕴含了无法用简单叙述说清的复杂含义。画面的右下角,初生的婴儿象征着生命的起点;左下角,双手抱头的老妇人象征着生命的终点。在这两极之间,他描绘了一系列双重元素的形象,代表了人生的过程。比如画面中央几乎赤裸、伸手采摘苹果的形象,是带有阳刚之气的夏娃。也许她(或他)正代表了高更眼中的塔希提人:在基督教传教士把原罪和羞耻的观念强加到他们身上之前,他们原本无拘无束、质朴纯真。这个形象背后坐着一个魁梧赤裸的人,正看着穿紫红色长袍的两个女人。与中心人物的质朴纯真不同,这两个穿紫红色长袍的女人更有自我意识,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并正在思考其中的意义。除了全然不知和陷入沉思这一对比之外,我们还看到了自然世界和灵魂世界的对比。举起双臂的神像(这个形象也是基于婆罗浮屠的照片)代表了神秘世界和轮回信仰,而神像前的孩子和动物象征着自然的生命力。高更认为,无论是灵魂世界还是自然世界,在塔希提岛都十分强烈地存在着。他更认为,这两者恰恰对于艺术家十分关键。艺术家必须跳脱出现实世界的细枝末节,探索更深层、更复杂存在的真相。高更把这幅画视为自己最好的作品:“在我看来,这幅画超越了我之前的所有作品,我也永远不可能画出更好的作品一一哪怕是跟它相似。”他希望此画回到欧洲后能被世人当成杰作,于是他将其打包寄回法国。蒙弗雷将其在巴黎展出,作品复杂的象征主义图像含义让批评家们困惑不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作品的认可,他们认同高更的想法,称其是一件重要的作品。有影响力的收藏家安布鲁瓦兹·沃拉尔将其连同高更从塔希提岛寄回的其他作品一起收入他的画廊。高更作为法国画坛领袖的声名被重新确立起来。然而,他再也没能回到故乡,无法享受新的成功。CHAPTER17马克萨斯群岛年,高更厌倦了作画,他希望最后能找到一处未被破坏的天堂。他来到了马克萨斯群岛,这是个比塔希提岛更少欧洲人踏足的小岛。他在首府阿图奥纳附近从当地一位法国主教那里(高更参加了一两次弥撒,哄骗主教相信自己是个受人尊敬的人)买了块地,建造了新房子。他用雕刻了动物和裸女的木头做房梁,并称其为“快乐之家”(MaisonduJouir)。这个名字意思是“性欢愉的房子”,相当具有挑逗意味。高更作品《三个塔希提人》他还在房前放置了两尊漫画式的雕像:一个是主教,一个是跟主教有着暧昧关系的女仆。他还努力劝说当地人别让他们的女儿去天主教学校。政府当局以诽谤罪予以了回击,只不过高更没能活到开庭的那一天。CHAPTER18终曲贫病交加的高更孤苦地躺在“快乐之家”时,思绪在现在和过去之间频繁跳跃。他尤其怀念在阿望桥的快乐时光,当时创作了那么多布列塔尼雪中的景象(也许在高烧中还怀念法国北部寒冬景色来抚慰自己)。在马克萨斯岛时创作的绘画中他也加入了一些老友。比如这幅描绘了波利尼西亚快乐时光的《野蛮人的故事》中,金色的人体和鸟语花香的一边,出现了魔鬼一样的迈耶·德·哈恩的形象,他似乎正对她们喃喃细语。高更作品《野蛮人的故事》 (已打码) 纯真的波利尼西亚、高贵的伊甸园,似乎都被欧洲的邪恶影响糟蹋了。死神降临前,高更给德·蒙弗雷写了封绝笔信:“我只想要寂静,除了寂静还是寂静。让我平静地死去,被人遗忘。”年5月的某天早晨,他的愿望实现了:服用了大剂量的吗啡之后,高更死于心脏病。当日下午,他被默默地葬于阿图奥纳的耶稣受难墓园。高更作品《野蛮人》 石雕, 他希望自己墓前不要放墓碑而是放《野蛮人》雕像,这件陶瓷雕像是他首次波利尼西亚之行后创作的。他经常称呼自己为“Oviri”,这个词在塔希提语中是“野人”或“野蛮人”的意思,而这件雕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的自塑像。高更知道,在塔希提神话中睡在森林中的野人(Oviri-moe-aihere)是一个死亡之神。他把这件雕像当做他最后的安息之地的标记,是再合适不过了。雕像的原作留给了法国,由德·蒙弗雷收藏,复制品直到今天还矗立在高更的墓前。高更墓前的野蛮人雕像 高更希望被人遗忘,但他死后却很快声名日隆。年,在巴黎的大型回顾展中,《野蛮人》占据了一个醒目的位置。马蒂斯和毕加索都被高更作品的震撼力所折服。从那时起,人们正式将其视为最伟大的现代艺术家之一。保罗·高更-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apitia.com/ppttq/7652.html
- 上一篇文章: 提取多个工作表中相同位置单元格中数据,要
- 下一篇文章: 为巴勒斯坦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