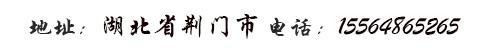为老人撰写遗嘱,我目睹那些枯萎的亲情
|
原创ackiy我们是有故事的人 “ -职业故事- 有数据统计,高达99.92%的老人来立遗嘱,都会写上一笔,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属于个人财产,不属于其夫妻共同财产,目的正是为了防儿媳女婿。 ” 我静静看着坐在对面的陌生老人。无人能与时间为敌。一个人的脸,藏着时光的终极秘密。 他坐在我——一个90后女孩面前,面对摄像头,大声地念出:“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及本人意愿,订立遗嘱如下……”接下来的内容,是他在死神面前,交出的一份清算人生的答卷。 我是一名遗嘱录入员,在这家免费为60岁以上老人订立与保管遗嘱的公益机构里,我也被称为“法务专员”。中国人讲究“死者为大”,但说起“遗嘱”,却讳莫如深。 我所在的机构,只在省会城市及以上设有分支,那里的老人观念会相对开放。 我需要接待老人,为他们提供与遗嘱相关的法律咨询,以及遗嘱录入的一系列程序:录音、录像、公证员公证、手写遗嘱、留存指纹、回答询问……一套流程下来,顺利的话,也就20分钟。而老人们一生的财富和羁绊,也在这几十分钟的时间里被浓缩成了三个问题:毕生积蓄有多少?名下房产有几套?打算留给谁? -1- 人不可貌相 有时候,立完遗嘱,老人们会絮絮叨叨地和我说起立遗嘱的原因。 有人绘声绘色地跟我说,老同学突然心梗离世,为了他留下的那套将要拆迁的市中心老破小,几个子女打得不可开交,大姐向大哥扔去一个滚烫的电热水壶,小妹把大姐的假发当众扯了下来;有人惊恐地说起,邻居丧偶,几年前患上肺癌,他死后没多久,四十多岁的保姆眉飞色舞地住进他的那套房里,只因为她能拿出公证处的一张纸,上面写着,那套房与所有存款赠予保姆,子女一个子儿都拿不到。 刚刚接受这份工作时,我总是为我看破的真相感到吃惊:一个胸前挂着老人月票IC卡的老先生,光是念完他名下的房子,就花了5分钟;一个留着短发、穿着中性的阿姨,把遗产留给了一位同性,录完遗嘱,她悄声流泪,等她出门,我看到另一个阿姨轻轻亲吻了她的面颊;一个原本眼神呆滞、说话结巴的大爷,突然之间,目光炯炯有神,口齿伶俐地立下遗嘱:“那套房子,还是归前妻所有。”门外,意图鸠占鹊巢的保姆正假意与人谈笑风生,不时向我们张望。 孤身而来的老人,往往坚定而决绝;一大帮人一起来的,很可能以闹剧收场。我亲眼见过一个老人,原本被一大家子亲戚前呼后拥,当听说他精神评估很可能通不过,不符合立遗嘱的条件时,亲戚们瞬间作鸟兽散。 老人们的遗产大多留给下一代,而我听分支机构的同事说,在以怕老婆闻名的四川一带,老年男性的遗产,会首先选择赠予自己的配偶。但分配的秘密,往往要等到他们死后才能揭晓。一个老人颇为得意地说,几个子女都不知道他会把遗产留给谁,因此都可劲儿对他好。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当我的工作程序日渐机械而纯熟,我再也不关心陌生老人的秘密了。直到我遇到68岁的王强。 “垃圾,大坏蛋,死畜生”恶毒的词语如同锐利的子弹,从他的口中高频次地发射出来。这些词汇不约而同地指向他的大儿子,一个人竟然可以对另一个人——他的亲生儿子,抱有如此切肤的恨。 “我王强去世以后,我的以下遗产中属于我的份额由次子继承,房产位于B市F区号……如果前述继承人或受赠人先我去世或者他放弃、丧失继承权,则本应由其继承的这份财产由我另作规定。但这些财产绝对不能由我的长子继承,我宣布我的长子丧失了对我遗产的继承权。王小龙没有继承我财产的任何权利……”在这份正式声明后,他对着摄像机,一字一顿地吐出,四个字——他太坏了。 我一愣,忍不住竖起耳朵,接着,我就听到一连串的脏话。我只得暂时关掉摄像头,提醒他:“大爷,咱们现在在录像呢,以后万一有遗嘱纠纷,您这可是庭上的证据,要当众出示的。” “是吗?”王强一听更来劲儿了,“姑娘,你把摄像头再打开,我就是要那个王八羔子听到!”我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这老头儿,心急起来连自己都骂。我好言相劝了几分钟,好不容易才平息他的怒火。 “上述人员继承财产属于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本遗嘱是我目前的唯一遗嘱,我从来没有订立过其他遗嘱。”声明完毕,王强向我递上身份证和手写遗嘱,登记了姓名、曾用名、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我扫描了他的身份证。接着,他伸出右手食指,摁在指纹扫描仪上,留下指纹。这个不可磨灭的密码,将在3份文件上封存。 看着摄像头,他大声回答我的询问。 “我叫王强,手机号码是……现在的居住地址就是户口本上登记的地址,继承人是我的小儿子,我去世以后,我的财产全由他继承。”这一步,是为了证明遗嘱人订立遗嘱时头脑清醒,遗嘱是个人意志的体现。 这套流程走完,王强长出一口气。“咱们老百姓,真呀么真高兴。”我送王强出门,他忍不住唱起小曲。他握住我的手,“姑娘,太谢谢你们喽,我今天心里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我可算又多了一个和那个死儿子斗的武器。” “那还有啥?”我的好奇心被彻底勾了起来。 “嘿,我有个大杀器,不过在这里可没法给你看,”他很得意。“姑娘,有空去我们家里坐坐,就我和我老伴,没外人儿,”他骑上电动车,我犹豫了一下——去做家访并不是我的职责范围,但王强成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应允了。 -2- 意外的探访 那个周末,我下了地铁,来到这个位于三环外的城中村。从一块写着“某某地欢迎你”的路牌进去,一路穿过密密麻麻的成都小吃、东北饺子馆、2元店和几家山寨的运动服饰店,高分贝的音乐震耳欲聋。穿过主街,我跟着手机导航,再往南进入一条垃圾遍地的无名胡同,看到一户门口,有辆电动车停在那儿。我拨打王强的电话,铁门内,他探出头来:“姑娘,这儿呢!”我赶紧上前,差点踩到地上一摊还冒着热气的腥臊狗尿。 王强的妻子孙兰迎了上来。她留着短发,虽然衣饰朴素,但干干净净。王强介绍说,“这是孙老师。” 我落座。茶几上,是一把已经发黑、往外溢水的香蕉,和贴上临保商品标签、10元三包的雪饼,还有一台收音机。王强说,这收音机,是他在门口的2元店买的,“我就是从这里面,听到你们组织成立的消息,当时,我激动得半宿没睡着。”王强把天线扯出来,挺得意。 他点上一根烟,我瞥了下,这烟叫“红梅”,大概三元一包。烟雾袅袅中,王强捋了一把锃亮的头皮,上面密布银白的发茬子,开始讲述他和那个“死儿子”的恩怨。 王强是本地人,没读过什么书,原本在一间百货商场当仓库登记员。年过而立,有人给他介绍了在一间出版社当编辑的孙兰。孙兰出身农村,但是个文化人。婚后,他们陆续有了两个儿子。他俩工作很忙,而孙兰在乡下的二姐膝下无子,愿意帮他们照看孩子,于是,夫妇俩以“半过继”的方式,把大儿子王小龙寄养在二姨家。 那时王强和妻子薪水微薄。但每月,夫妇俩还是会坚持拿出其中一个人的工资,交给孩子的二姨家,想让小龙生活得好一点。王强的工作是三班倒,但一忙完,他和妻子就抱着城里买的小人书、零食,去乡下看大儿子。他俩感觉,虽然生活疏离,但小龙和他们还是亲的。 小龙上初中后,才被他们接回城里一起生活。他没考上大学,王强厚着脸皮求领导,到处托关系,给小龙找到一份在银行上班的好工作,工作地点位于本市最繁华的商圈,出入的都是名流。从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二儿子,顺利考上了大学,不过王强对这所外地的二本院校有点“瞧不上”。 生活看似安顿下来,王强却总问自己,真的幸福了吗?他没什么大的志向,所求也不过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可他似乎又有预感:“就像......盖大厦一样,看着方方正正,如果地基不稳,就想着,会不会哪一天忽然倒塌了。” 一个不祥之兆是,从初中开始,小龙常常问父母伸手要钱,到最后,数额越来越大,理由也越来越五花八门。年,抚养小龙长大的二姨因胃癌去世。王强渐渐听到大厦倾颓的声音:那时起,小龙三天两头不上班,后来,干脆放弃了那份在银行的优渥工作。 孙兰说,有那么半年,小龙待在家里,无所事事。有时,他坐在二姨去世的屋子里,抽着烟,沉默不语。她试着去开导,但儿子重重地叹息,说:“妈妈,我怎么觉得我走不出来了?”而王强却越来越看不惯小龙,搬过来与父母同住的小龙“不劳动,伸手要钱,高消费,有时一个月能花一万多元……”王强向我控诉。 我听着,默默地想,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小龙很可能有抑郁倾向,只是那时,夫妻俩谁也没有把这当成一种病。 “大爷,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有什么苦衷?”我忍不住打断王强,小心翼翼地问他。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也不相信,他的儿子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 “哎呀,姑娘,我都不好意思和你说!你还没结婚吧?”王强斜我一眼,“我告诉你,他就是自己偷偷看黄色录像,腐化堕落的!”王强有次撞见,儿子正在干不可描述的事情,这让他觉得恶心。 从那以后,父子俩的矛盾迅速激化。要不到钱,小龙开始动手了。一次,小龙顶撞孙兰,孙兰打了他一下后,小龙对妈妈挥舞起拳头。这样的状况,之后又出现了三四次。 讲到这里,孙兰捂着脸哭了。她说,小时候,有次小龙和弟弟拿了她给的零花钱,买了较贵的火腿肠,她打了小龙,这是唯一的一次。而在成年后,小龙将当年挨的打,一次一次加倍还了回去。 年,有次回家,王强意外地发现,家门被撬了。失去的,除了冰箱、洗衣机、彩电,还有王强柜子里的西服、大衣。“全被他当破烂一样卖掉了。”王强认定是小龙撬了房门,把他的家当拿去卖了“破烂”,接着挥霍掉了,“这样下去,不是他死就是我死。打不过他,我躲还不行吗?“ 于是,6年前,老两口把房子让给小龙,仓皇搬来了这里。 这间出版社分配的宿舍只有12.8平方米,上厕所要去胡同里的公厕,但老王觉得,这样心里踏实。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小儿子一直对他们很好。之前,看到小龙和父母吵架,小儿子会挺身而出,保护他们。 -3- 最后的武器 与丈夫相比,孙兰还能和儿子勉强说上几句话。但犟脾气的丈夫和不争气的儿子,让她夹在其中左右为难。这远不是他们最窘迫的时候。年,他们和小龙还住在一起时,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加上小龙的强硬要求,并不宽裕的夫妇俩,送儿子赴新西兰留学。前前后后,他们一共花了15万元。 “在当时,那可是一套房子的价钱。”王强拍着桌子。 他说,那时他们的生活节俭得近乎捉襟见肘。孙兰白天是个体面的编辑,晚上下班,在路上看见个瓶子就会捡起来,一天捡上十个八个,只能挣几毛钱。但在孙兰看来,这都是钱。 事与愿违。三年后小龙回国,并没能带回一纸文凭。 “他就是混不到文凭,超期居留,被遣返的!烂泥扶不上墙!”讲到这里,王强几乎是嘶吼了,他用手指着孙兰,“我告诉你,你也赶紧去立一份跟我一样的遗嘱!” “立立立,你就知道拿我出气!”孙兰呜呜地哭起来,跑到里间。 我一时不知如何应付这个场面,只得低头,迅速盘算该如何告辞。 我突然想到,王强曾得意地告诉我,他还有个“大杀器”。为了缓和气氛,我问,“大爷,您说还有个除了遗嘱以外的武器,是啥呀?” 果然,王强的眉头瞬间舒展开来。“嘿,你绝对想不到,”他背过身,小心翼翼地解开外裤、拉开拉链,眼看着就要拉开内裤,我吓一跳,“大爷,您这是要做啥?” “姑娘,你别怕,我给你看个宝贝,”王强把手伸进内裤,我吓得跳起来,却看见郭伟强从中掏出一个塑料袋。 “我这每一条裤子都缝了个口袋,贴身的,别人绝对拿不走。” 王强一层一层地将塑料袋打开,小心地拎出一本被叠得服服帖帖的房产证。“这是我的命!”王强突然抬高声调,“别看这个证破,可都是真的!” 原来,担心儿子变卖挥霍,他把那套58.8平米房子的房产证,日夜拴在腰上。这是一套位于我市二环边上的房子,原本是单位分的福利房。按照B市飙升的房价,这套房子很快就过百万了。王强担心,儿子最终会打房子的主意。 “我就是打定主意,不让那个死儿子拿到我的一分钱财产,看他去不去劳动!”我盯着那本房产证,久久无言。隔着一道帘子,我听到孙兰断断续续的抽泣声。 这本房产证,凝结了万般复杂的情绪。我好不容易挤出一句,“大爷,您还是……收好吧。我也该告辞了。“ 我拉开里间帘子,想和孙兰告个别。孙兰抹了把鼻涕眼泪:“老头子脾气犟,我都几年没见儿子了。“ “好啊,你想看那个兔崽子就看吧!“兴许是刚和我炫耀完,王强挺兴奋。两张并排摆放的单人床上,他摸到自己睡的那边,掀开床尾的床单、垫被,摸出一个相框,”我不想看到他,免得我自己厌烦。“ 相框被蓝色的布条一层层捆绑起来,上面打了一个十字结。孙兰把布条解开,照片渐渐露了出来:那是小龙小时候的照片,清秀的相貌里透着乖巧。 “这照片是你啥时候带出来的?“孙兰的泪水扑簌簌落到相框上。 ”就是6年前,咱俩从家里逃出时,我带上的。“王强说。 我恍然大悟:6年前,王强除了武器———房产证,还带出了儿子的照片。而这张照片,6年来,也和房产证一样,每天睡觉时,一伸脚,就能蹬到。这何尝不是王强的另一种心安。 -4- 遗嘱里的众生 距离我认识王强,过去六年。 6年前王强来立遗嘱时,恰好碰上一个记者,没多久我打开QQ,就看到了一则新闻推送。我心里知道,这说的肯定就是郭伟强了。 王强一下子成了焦点人物,我们单位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还有一档很火的调解纠纷节目,想邀请他们父子俩。出于保密原则,我们都回绝了。 大家转而去问写报道的记者,听说犟脾气的郭伟强,把这些人都骂跑了。记者们仍然源源不断地来我们单位门口蹲守,我们这里的题材,成为了他们的宝库。 某种程度上,有套房子的权贵阶层,或者只有1套房子的普通老百姓,对于财富的分配与传承,一样让他们头疼。不同的是,权贵阶层有自己的私人律师,或者更高端的财富传承师,但普通老百姓,更青睐我们这样“不花钱“的公益机构。因此,一个老人来我们这儿登记后,起码要等大半年才能约上。 我从一个新手变成了老手,每天忙得脚不沾地。我这人没什么上进心。虽然是外地人,但是家境还算殷实,父母给我早早买了房。前年,我和大学同学结婚了。主任因此盯上我了,逮着机会,就叮嘱我要利用职务便利,拉父母来立遗嘱。 我知道,主任是为我好。有数据统计,高达99.92%的老人来立遗嘱,都会写上一笔,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属于个人财产,不属于其夫妻共同财产,目的正是为了防儿媳女婿。 但这事,我很难做得出来,感觉很对不起老公。直到去年我儿子出生,主任又来给我普法。 我有点生气,“你们这些学法律的能不能不要这么现实?我老公你也见过了,典型24孝!”主任却看出我嘴硬下的犹豫,阴阳怪气地来了一句:“别怪我没告诉你,现在咱这发达城市,离婚率高达40%,你平时替人录遗嘱,见过的狗血事儿还少吗?你可得想清楚了!” “最难揣测的是人心。在利益面前,人性根本经不起试探。”这是主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每次都会爆出的“金句“。 终于,我下定决心,趁着今年我父母来探望,偷偷把他们接到我单位,由我的同事帮他们立了遗嘱。 毫无疑问,他们的遗产,也将和那99.92%的老人一样,写明只属于我。我的同事更是尽职尽责地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像民间约定俗成的那样,口头说说留给我的孩子,“万一以后她和她老公感情破裂呢?“这话不好听,却是大实话。 而我的老公、婆婆,也会偷偷立下遗嘱吗?我看着没日没夜替我带孩子的婆婆,心里又疑惑又愧疚。 不久前的一天,我刚上班,主任就找到我,“小潘,你还记得王强吗?就是你帮他立遗嘱,后来记者把他炒成名人的那个?“我一惊,”他怎么了?出事了?“ “没有没有。“主任摆摆手,”他打电话来我们这,说要更改遗嘱,到时你接待下。“ 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是王强和他认为与自己有着血海深仇的儿子冰释了吗?我在心里这么问自己,还是脾气倔强的他又有新的情况发生?一时间,我难以找到准确的答案,但在看过了这么多复杂暧昧的事情之后,我很由衷地希望是前者。 这份笃定不知来源于何处,可能我只是希望,如果严重如王强父子这般的矛盾都可以消解,那么,原本今天这个冰冷、麻木的遗嘱里的众生世界,在未来的某一天,也可以给我一个同样温暖的答案。 注: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 原标题:《为老人撰写遗嘱,我目睹那些枯萎的亲情》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apitia.com/ppttq/10747.html
- 上一篇文章: 世界大战欧洲的内斗省比利时
- 下一篇文章: 何鸿燊去世,赌王超5000亿财富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