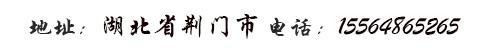对话保罗middot索鲁疫情阻止
|
白癜风预防 http://baidianfeng.39.net/a_wh/160216/4771446.html 疫情阻碍了国际出行,旅行作家们的生活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保罗·索鲁,因上个世纪花一年时间行走中国后完成的游记而饱负盛名的美国作家,在疫情期间开展了一次横跨美国的公路旅行。《纽约时报》记者在他位于夏威夷的家中见到他,聊起疫情的旅行,聊起旅行文学的变化,还有时光在这位老人身上留下的痕迹。 ——编者按 一连6天,美国著名游记作家保罗·索鲁(PaulTheroux)一直在吃煮鸡蛋、用微波炉加热的木豆和葡萄酒。 去年感恩节的前一天,他开着租来的JeepCompass指南者从马萨诸塞州科德角(CapeCod)出发,横跨美国前往洛杉矶市,他在那里有一座自己的房子。到了洛杉矶后,他把成箱的书信手稿交给亨廷顿图书馆(HuntingtonLibrary)档案室,然后启程飞往他的另一个家:夏威夷。 在过去30多年里,保罗·索鲁时不时会回到瓦胡岛居住。 索鲁回忆说,受新冠疫情影响,所到之处尽是一派萧索的景象。他在俄克拉何马州萨利索(Sallisaw)路过几家空无一人的汽车旅馆,在新墨西哥州图克姆卡里(Tucumcari)睡了一夜,又在田纳西州一个高速路服务区独自享用了感恩节大餐。公路旅行的最后一天,他则去了亚利桑那州金曼(Kingman)的一家In-N-Out汉堡店。所有地方都冷冷清清。到了晚上,他会像往常一样拿起纸笔,记录白天的所见所闻。 这天,他在位于夏威夷瓦胡岛(Oahu)北岸的家中接受视频采访时说:“就像是对美国做了一次全景拍摄。”在过去30多年里,他时不时会回到瓦胡岛居住。 保罗·索鲁年出生于美国,他是当代最著名的旅行作家之一。 索鲁在今年4月迎来了80岁大寿。他的作品被如今已经白发苍苍的一代背包客奉为圭臬,他的中国、非洲、南美洲游记被人们翻得破破烂烂,在过去的岁月里激励他们勇于探险,让他们在蚊帐之下倍受鼓舞。他的最新小说《怀梅阿的海浪下》(UndertheWaveatWaimea)在4月由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社(HoughtonMifflinHarcourt)出版。他最知名、也是本人最喜爱的作品《蚊子海岸》(TheMosquitoCoast)已被改编成电视剧集,于4月底与观众见面,主演则是他的侄子贾斯廷·索鲁(JustinTheroux)。 或许现在是个不错的时机来回顾索鲁彪悍的一生,盘点他数量惊人的作品,但在索鲁看来,他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疫情爆发前,他就打算前往非洲中部旅行。目前,他正在埋头创作另一部小说,为一本新的小说集做最后的修订。似乎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写过了几本书了:“大概50来本吧?”(确切地说是56本。) 保罗·索鲁在夏威夷家中的书房里。 索鲁素以创作旅行文学而闻名,但其实在年代初,年轻的他出版了几部小说后,发现自己才思枯竭,迫于无奈才抓住了旅行文学这根救命稻草。当时他决定坐火车横跨欧亚大陆,先从他旅居的伦敦出发,穿越中东一直来到东南亚,最后取道西伯利亚大铁路返回伦敦。索鲁基于这段令人疲惫的旅程写下了《火车大巴扎》(TheGreatRailwayBazaar)一书,其销量已超过万册。无数后来者追随他的足迹,出版了大量类似的作品。 仅在过去10年里,索鲁就创作了多部游记。《蛇之平原》(OnthePlainofSnakes,年出版)记叙了他孤身自驾穿越墨西哥的经历(索鲁一向喜欢独自旅行);在《美国深南之旅》(DeepSouth,年出版)中,他探索了美国最贫穷的一些地区;而在《前往非洲丛林的最后一趟列车》(TheLastTraintoZonaVerde,年出版)里,他故地重游,回到了自己在年代作为和平队志愿者去过的地方。 在他位于夏威夷的家里,保罗·索鲁与他饲养的鸡和鹅在一起。“养了鹅,就再也不需要割草机了,”他说。 近年来,以外人的眼光对当地评头论足的旅行文学渐渐失去了它的魅力,取而代之的是像伊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ethGilbert)《美食,祈祷,恋爱》(Eat,Pray,Love)这样的旅行回忆录,后者既描绘了异国风土人情,也呈现了作者的心灵之旅。对此,索鲁为自己的写作手法做了一番辩护。接受采访时,他正坐在书桌前,桌上散落着不少旅行纪念品,包括几尊小佛像、在巴厘岛旅行时别人送给他的猴子贝雕,以及来自波利尼西亚的木制武器。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与他人面对面,和对方产生共情。要置身另一种文化,感受它、忍受它,忍受旅途的艰辛和烦恼,这些都是关键。”他引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的话说:“我相信如果可以准确把握当下,就能预测未来。”在索鲁的写作生涯中,他曾把奈保尔当作良师益友,也曾与他反目成仇。索鲁也同意奈保尔的观点,他说:“不需要预测未来,只要把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东西写出来,你就成了一名先知。” 索鲁的新作《怀梅阿的海浪下》和根据小说《蚊子海岸》改编的电视剧集均于今年4月问世。 但如今,并没有多少人追崇先知,特别是那些总爱对其他文化评头论足的先知。索鲁似乎对此心知肚明,或者说,他至少知道自己的那套写作方式已日渐式微。 他的最新小说围绕瓦胡岛北岸一个年迈的冲浪者乔·夏基(JoeSharkey)展开,人物原型则是他在自家附近海滩上结识的几个冲浪爱好者。夏基深感那些坐拥大额赞助的年轻人渐渐抢过了他的风头。冲浪对他而言是一种生活方式,劈破斩浪是他毕生的追求,也倾注了他对海洋的满腔热忱。 在索鲁眼中,冲浪是他人生的隐喻。他唯一渴望的是不受干扰地写作,不被窗外的汽车报警器打断思绪,不必为支付账单而发愁,除了日复一日地坐在写字台前,他不需要为了赚钱做其他任何事情。从许多方面而言,索鲁已经实现了他的愿望。但就像已过了巅峰期的冲浪者一样,他难免感到自己被世人遗忘,意识到冲浪带来的纯粹的快乐已经不容于世。他担心自己的作品无人问津。 “以前我是炙手可热的名人,我是个朋克,”索鲁说。“朋克终究会变老,时光一去不复返。每个作家都有这种感觉。他们也许会否认,但他们都有这种感觉。” 索鲁在客厅里堆放了许多书籍,有几本是他朋友史蒂夫·麦柯里的作品。 索鲁一点也不像传说中的那样脾气暴躁。书评家经常会提起他尖酸刻薄的文风,好像他总是高高在上,极力挖苦他在旅途中遇到的人和他笔下虚构的人物。就拿史蒂芬·金刊登在《纽约时报书评》(TheBookReview)上针对索鲁年稍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故乡》(MotherLand)的评价来说,他认为这部作品是“一种自顾自的傲慢与自怜”。 索鲁知道读者或许会觉得他脾气古怪,但他觉得问题可能出在读者身上。他说:“你不可能当一个暴躁的旅行者,不然哪里也去不了。你会被人杀掉,会受到侮辱,你是没办法旅行的。你得和别人友好相处。别人说我满腹牢骚,也许因为我直来直去,不拐弯抹角,于是就有人说我为人刻薄。” 英国游记作家兼小说家乔纳森·拉班(JonathanRaban)是索鲁的老友,两人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常交换手稿。拉班认为,书评家没有意识到索鲁的写作风格发生了重大改变。他表示:“他的早期作品里有那种讽刺劲儿,那种犀利的笔触,还有一成不变的外来者冷眼旁观的视角,相比之下,保罗在最近几部作品里展现了我以前没有见过的人性关怀。” 他指出,索鲁在年发表的一篇散文里讲述了一只名叫“威利”(Willy)的宠物鹅的故事。索鲁将它一手养大,临死时又把它抱在怀里,看着它碧蓝的眼睛渐渐失去光泽,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伤感与柔情。拉班认为这篇散文一如索鲁最近的几部作品,说明他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从尖酸讽刺到温情满满,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我以前是个朋克,”索鲁说。“朋克终究会变老,时光一去不复返。” 年龄也对他产生了影响。索鲁看到了年龄的优势,就好比年迈的冲浪者体力下降,他就不得不琢磨更高明的冲浪技巧。毕竟,保持着世界最高冲浪纪录的人是将近50岁的加勒特·麦克纳马拉(GarrettMcNamara)。而八旬老人出门旅行也有优点。有的文化中,人们对老人视而不见,这在很多情况下对索鲁是有利的。 而在他去过的其他地方,人们对老人尊重有加。索鲁说:“他们要么忙不迭地给你让座,要么就对你视而不见。” 那么他接下来想去哪里旅行呢?索鲁回答道:“我有很多想去的地方,也有很多地方从来没去过。我没去过斯堪的纳维亚,但我不想到那里去。” 他最渴望的是重游故地。回到年轻时去过的国度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成为生命中的标尺,也可以用来衡量社会变迁。 索鲁表示:“它能告诉你世界发展的动向。世界会发生哪些变化?重访一片熟悉的土地,你就能推断出答案。回到英国,回到马拉维,回到中国,回到印度,真是太有意思了。你问我最想去哪里旅行,我最想到去过的地方再看看。”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apitia.com/pptwh/8369.html
- 上一篇文章: 猪年新计划玩猪治焦虑睡猪栏一口吃掉一
- 下一篇文章: 没事跳个悬崖,这样简直太刺激快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