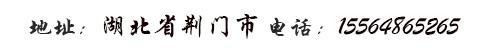李晁森林启示录读安妮middot普
|
治白癜风成都哪家医院好 http://disease.39.net/yldt/bjzkbdfyy/6083892.html 森林启示录 读安妮·普鲁《树民》 文李晁原刊于《上海文化》年3月号 BOOK 安妮·普鲁《树民》 《树民》最初的成果出现在年,这一年《纽约客》发表了安妮·普鲁以森林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粗暴行为》。小说的源头更可以追溯到十五年前,这是一部“蓄谋”已久的作品。这一次作家从边疆视野迈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北美大陆开发史。这是作家首次处理庞大题材,跨度三百年的时间进程,作家让两个家族更替纠缠,而故事的依托与景观来自于小说的恒定坐标——森林。这一焦点凸显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如果说边疆题材让安妮·普鲁投身的是一处失落的地带,那么到了《树民》就回到了这一失落的源头。小说见证了人类轨迹对这片土地造成的影响,这影响最终也反噬了人类自身,这是一部完整表达出“失落”过程的史诗性小说。在与黛博拉·瑞特斯曼的访谈中,安妮·普鲁道出了创作之源:大约十五年前,那时我经常开车出游,当我以不同的路线穿越大陆时,我路经一个位于密歇根上半岛的废弃小镇。这个地方灌木丛生,只有一座建筑,一个废弃的多用途商店。在长满灌木和杂草的山坡上,我看到一个指示牌,大致是说,上个世纪此处生长着世界上最大面积的五针松森林。森林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这个指示牌,从那一刻起,我开始考虑一部与滥伐森林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小说。小说从17世纪末讲起,追随两位法国移民的步伐,开始以两个家族的交错发展见证了北美近代的历史变迁。北方乃至东西部森林的盛衰(长达三百年的砍伐)成为这部小说的浓烈背景,从两个家族面对森林的不同行为和结果来看,这是一部深刻涉及人文与环境的小说,两者休戚相关,乃至一出出悲剧,都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自我与自然的关系。小说的努力接近了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所言:“必须试着从非人类的角度来审视人类自己的行为。也就是后退一步,看看当初在自然界其他生物眼中人类是怎样的。”在小说的尾声处,第一代闯荡森林的移民勒内·塞尔的子孙——萨帕蒂西娅·塞尔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也可视作对唐纳德·沃斯特的回应),“倘若从第一位原始人直立身体,以新的视角审视世界时起,一切就已经太晚了呢?”这声音也在夏尔·凯迪的后代,杜克父子公司最后的“血液”查理的临终笔记中体现,“人类如同君主般行事。他们决定万物的兴衰枯荣。我认为人类正逐渐演变为一个可怕的新物种,而我很抱歉自己也是其中一员”。我们无法阻止缘起的事物,甚至我们仍然无法阻止人类继续前行的步伐,这是当下的困境与无奈。是《树民》将这一困境推到了足够久远的时候,那疯狂被点燃的源头,让我们目击人类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面临如今的境况的。小说最触目的场景,一方面来自对资源的疯狂掠夺,对森林的无尽索取。这不仅是对利益的夺取,更表现了来自欧洲的自负——人类主宰万物的“天赋人权”;另一方面这攫取的过程也是对原住民(印第安人)的粗暴压榨乃至血腥统治的历史。从这一角度,印第安人的存在和树木并无二致,消失的人口如同消失的森林一样令人震惊。查尔斯·达尔文在《贝格尔号航行日记》里写道,“欧洲人走到哪里,死亡似乎便在哪里追随着土著居民。放眼望去,南北美洲、波利尼西亚、好望角和澳大利亚无一例外。”这是多样文化在强势“文明”入侵后的逐渐衰落过程,这衰落的危机首先来自人口的骤减。“仅仅几年时间里,他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人,数也数不清。据说他们原来的世界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便已不复存在了。”“再过四十年他们将不复存在,就像有史以来从未这么少过,甚至才不到五百人;在白人到来之前,他们曾有超过十万人。”印第安人口的消失与森林的退却,代之的却是移民的汹涌涌入。据统计,从年到年就有四波说英语的移民迁徙到现今美国的领土上,而—年,更有五千多万的欧洲移民奔赴海外。“大量到来的欧洲人的数目很快就可以和这些鸟儿抗衡了”,作为调侃,这一不可动摇的潮流甚至被最早置身殖民地的人和原住民共同鄙视,仿佛他们是另一种“野蛮人”。吊诡的是,最初到来的白人也同样被如此看待。“白人走过的地方就会长出坏植物”。出于开垦的需求,后续的移民们盲目地放火烧毁森林,然后迅速看着土壤枯竭,这是恶性循环的开始。小说还借牧师掌管的寄宿学校这一微小的存在,道出了外来文明的虚伪与残酷。埃加的遭遇暴露了“寄宿学校的邪恶作为和政府监管的缺失永远地玷污了任何以文明和礼仪自我标榜的英裔加拿大人”。这一切片,让整个大陆的“文明”带着浓烈的原罪,且这罪孽延续得如此漫长,从起源的新教徒移民开始,直接迈进了20世纪。这原罪从何说起?或许可以追述到西方的人文主义,对自然的蔑视乃至征服自然是近代西方人的追求目标。笛卡尔在《论方法》里高喊,“让我们成为自然的主人与拥有者”。欧洲人在新大陆的肆意妄为,实践了笛卡尔的豪言,这一行径被放大到了无以伦比的地步,他们如同进入了一块无法无天的飞地,尽情施展着与个体欲望相匹敌的破坏能力。这足以使人对人类自身乃至其身后所代表的文化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这认识并不附身于我们往常以为的形式——“战争”之中,它直接散落在人类的日常生活里,又因它的隐形、不自知,乃至披着文明、教化这一光鲜的外衣,而更让人战栗。“那些孩子再也不会是纯粹的米克马克人了。”在新西兰,艾赫就曾询问过艾蒂安·塞尔米克马克人的故事,艾蒂安无言以对,“因为相比她所讲述的有诸多位神的毛利人的世界,他的故事会显得十分逊色而贫瘠。米克马克人遗失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传教士们的上帝。”这里的遗失,并非指事物的自然消亡,它是被外来力量剥夺的,是宗教、种族主义或其他。《树民》处理这一冲突充满着冷静又不乏哀伤的情感,但我们仍可以看到这冲突携带着裹挟一切的力量,“没有什么巨大到不能倒下的东西。当人类到来的时候,它们全都倒下了”。小说里有不少这样的提示,看上去是指森林,但又不单纯指森林,人类对自身同样施行了这一原则,这样的侵吞无法弥合,事实上也没有提供事后修补的可能,因这破坏来得足够彻底。小说结尾的觉醒正是来自对这一景象的忧虑,可以说小说的两部分力量(对森林的破坏及人类自身的挤压)最终都指向了对生态衰退带来的不安。在这里,人类对自身的“排异”从小说里隐退,《树民》的题旨变得更为清晰,人类的冲突演化为了更为深广的主题,即人与自然。在这一刻,自然才重新成为全新的主宰,它深切地影响到了不分族群、文化的每一个人。这一忧虑从哪里萌芽?我以为是以迪特尔·布赖特斯普雷歇的出现为标志的。他从一个为德国伯爵管理森林的角色介入新大陆的乱象中,他的现身直接导致小说出现了第一抹保护森林的色彩。后来的塞尔家族(回归印第安人)与凯迪家族(林业巨头)最终的努力——前者贡献了一位林业学博士,后者建立了苗圃并资助了保护行为——都无法阻挡一种事实,即承载漫长人类生存的地球很难回去了。这是萨帕蒂西娅·塞尔参观冰川后的悲观发现,但这并非小说的结论,它只提供事实,而人的主观行动,那些感觉事态紧迫的人已站了起来,并且,作为自然的一端,它的自我修复功能也预示着事态尚有乐观的一面。“人类社会系统适应他们的环境——生态系统,同时生态系统本身也在适应着人类社会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包括农业生态系统和城市生态系统)的自然部分,通过做出调整来应对人类的干涉,提高生存的可能。”这是自然的反弹与顽强,也是《树民》的客观角度和精神高度,这样的作用不言而喻,它指向了——唤醒。欲望,是《树民》的开端,也是被压制在生存线之下的开端。两个不识字的欧洲移民勒内·塞尔、夏尔·凯迪来到了广袤富饶的加拿大森林之中。此时,这片大陆尚没有国家概念,它只是殖民地,被笼罩在英法两大帝国的视野下,这是一道新的曙光(如果可以这么看的话),又因为确凿无尽的资源和可能全部占有的未来前景,它又确实算一道曙光。故事的主人公就这样义无反顾地踏了进去。从此,两个家族的命运开始抽芽。老实的勒内·塞尔想拥有的只是一处可以栖身的农场,这看上去退缩而又追求安稳的基因从此埋在了塞尔家族的基因里,又因与印第安女人玛希的结合,让这一脉络显得更为根深蒂固。塞尔的后代一次次出走,在伐木营中辗转求生存,又一次次地逃离,想寻求族人的拥抱,回归过往的生活,这顾此失彼间,属于米克马克人的生存方式乃至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流失了。但他们的天性仍未被“文明”所改造,他们哀叹森林的消亡,那赖以生存的环境被一次次的大规模砍伐而显得摇摇欲坠,对森林的神性认知与归属感,又悖论式地体现在了他们亲自参与的砍伐之中,这是痛苦的撕扯,他们偏偏又是其中的好手,比如昆陶、吉诺。昆陶晚年的回归,作为族长的存在已无法挽救这一式微的生存方式,他必须眼睁睁看着一切流逝。“正如昆陶曾说的,他们必须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当中,他们去往那里,因为他们已把它们的古老家园藏匿心头,不管要经历多少年岁。”这是昆陶的无奈,曾经的生活只能隐藏于心,迫切的只是眼下的生活,而这一切必须与新世界融合,这是以昆陶为代表的原住民的现实。小说的双线并进,在塞尔这一族的脉络里可以视作挽歌般的存在,他们的哀叹与身不由己,都被裹挟在历史进程中,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几乎从不抱怨,只是一次次转身离开……夏尔·凯迪的逃离与反叛精神与日后愈发凸显的野心同样根植在了后代之中,只是作为讽刺,这影响只存在于被他收养的儿子们中,他们在欧洲的孤绝处境与初入加拿大森林的夏尔·凯迪想奋力打造出一片天地的愿景没什么两样。这是一拍即合的合作。杜克父子公司(由凯迪父子公司改名)最终被这帮极具雄心的收养者所经营,这是凯迪的胜利。而他真正的子女,却总处在虚无之中,奥特赫迷失在对“科学”的痴迷中,当他带着众多被遗失的“发明”一脚踏入荷兰老家便不再回返,他唯一的女儿有着一半的印第安血统,她竟也是父亲的实验对象,对女儿碧娅特丽克丝的改造是其“疯狂”的表征。奥特赫堆积了太多的知识塞给这个混血的女儿,在培养她的计划里,唯一缺乏的就是爱,这种最基本的人类感情。“然而她渐渐明白,她自己并不是一个被爱的小孩——她对于奥特赫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附属品,用来实践他关于智力发展方面的设想。”种族的傲慢,畸形的念头,对未知事物的痴迷,是奥特赫留给我们的最后印象,他在小说中也如同迷雾一般消失。好在我们看到,长大后的碧娅特丽克丝并不是一个刻薄冷漠的女人,她的天性里仍保留有印第安人的宽容,对前来寻找丈夫昆陶的另一支子孙倾注了尽可能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apitia.com/pptzl/7601.html
- 上一篇文章: 和平之船环球邮轮太平洋世界号mid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