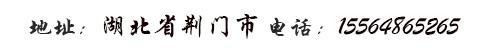二十年前去美国寻梦的那批人,后来遭遇了什
|
补骨脂素价格 http://m.39.net/pf/a_4345635.html美国,在曾经许多人的想象中,是“一个金砖铺地的花花世界”,然而当他们真正走入这里时,发现它同理想相去甚远,令人感叹其“最自由也最不自由”“最理性也最神经病”“肮脏势利也生机勃勃”。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是全世界留学生输出大国,人在异乡的故事每个人各不相同,但是一定有相似的感受。在出国或到一、二线城市求学谋生越来越普遍的今天,背井离乡似乎已经是一件寻常事。生存的重压伴随着漂泊感始终存在,“只要努力就能立足”的希望和“无论如何也无法融入”的失落交替。 二十多年前,出国还不是那么普遍的时候,有一批年轻人勇于选择挑战,率先踏上他国寻梦。这批人此后的遭遇,是一个时代下一个群体的肖像。今天这篇推文便是他们的故事,打破滤镜,勾勒一个色彩驳杂、充满真切触感的美国。 - 离岸流文丨凌岚节选自《离岸流》我二十多岁,大学毕业,一个从没有见过海的湖北汉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混在中国内陆省份走出国门的大学生中,来到美国,首站是洛杉矶。之前,我既没有坐过飞机,也没见过大海,离家最远的时候是到北京,那时我是县里唯一一个考进北京念书的。美国到底是怎么个样子,我们谁都说不上来,但坚信它是“一个金砖铺地的花花世界”,这是我们出国时的共识,但这句话到底是许诺,还是激励呢?或者就是老华侨和偷渡蛇头中流传的谣言?国航飞机抵达降落时,下面一半是太平洋,一半是沙漠,在红色的云蒸霞蔚中(后来知道那是工业污染和汽车尾气造成的雾霾),一个城市的平面缓缓露出庞大的峥嵘面目。我想起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我必须学游泳,仿佛洛杉矶是一个海洋。获得关于“离岸流”的知识,说起来缘起于我老婆红雨学车。出国离乡,扑面而来的事情太多,我们懵懂得像两只忽然被扔进水里的旱地小动物,我已经在洛杉矶这个海里住了四年,跟红雨结婚不到两年。红雨怀孕至六个月的时候,决定学驾驶。理由当然很充分,之前她学过车,已经通过笔试,就等着路考通过拿驾照了,我也愿意教她,但是我知道她心里害怕开车。红雨害怕洛杉矶的高速公路,这是她过去几年放弃开车,坐公交上下班的原因。按理说我们住在洛杉矶的银湖区,出门没几步就得上高速,她来美国也四年了,并不是初来乍到没见识过。但是,红雨对高速公路有恐惧情结,她个子本来就瘦小,坐在我们那辆本田车的方向盘后面,双手死死抓住面前的黑色轮盘,那表情就像溺水的小兽。她一紧张,车开得就慢,时速掉到六十英里以下,旁边的车一辆接一辆从左右两旁的车道呼啸地过去,超车的时候司机还回头藐视地看看她。这样一来她就更紧张,整个人缩得更小,本能地屏住呼吸,脸憋得通红。我怕她这样屏住呼吸时间长了,会当场在驾驶座上背过气去,那样我们就车毁人亡。怀了孕,红雨说无论如何她得拿到合法驾驶的驾照,家里有什么急事,她可以开车出门,就是不走高速,多绕点路也行。“不走高速”是她自我镇定的救命稻草,她的心思我明白,在我们当地的小街小巷里把车技练熟了,到时再上高速也就不会怕成那样了,熟能生巧。这样我们出门后就开始绕小路。去老费家做客后回来的路,也是这样绕行的。老费新购的康斗大屋买在洛杉矶的“上只角”,上高速走不过半小时的路,去一程我开车,加上周五晚堵车,也就花了四十五分钟。暖房结束时我喝醉了,当我一手推着从老费家取来的婴儿车座,另一手拖着一个二手学步器,手臂上挽着一大包费大卫的婴儿童装和没有用完的纸尿片时,红雨的眼睛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她果断决定:“我来开车。”她的手在我的裤子口袋里掏车钥匙时,手指隔着口袋布摩挲着我的腿,只几秒钟,我感觉很好,有点浮想联翩。她最近不喜欢我碰她。坐到副车座上,我把车窗打开,让夜里的凉爽空气吹进来,帮我醒醒酒。夏天的晚上南加州的风是温的,但是很干燥,吹在皮肤上很快把汗吸干了,很舒服。红雨端坐在方向盘前,手臂呈水平状各执方向盘的两侧,看着很正常。她举起的手臂带紧了衣服,勾勒出胸和腰的曲线,再次让我浮想联翩。车开过圣莫尼卡的“时尚好区”时,我们同时被街上漂亮房子的前面和后院吸引住了,忍不住回头看。红雨看一眼,就克制住自己不看,专心看路开车,我可以随心盯着看——白色的泥灰涂面的西班牙式房子,红瓦铺顶,低垂的鸡蛋花树;日式庭院,门前的纸灯笼;墨西哥式带屋顶的宽走廊,深棕色的方木柱子,红方砖铺地,爬满墙的红影树;沃尔沃车,宝马,奔驰敞篷车,雪佛兰科尔维特复古式跑车。然后我们都说住在这里离城多远啊,哪里有我们银湖方便!但是我知道其实我们是住不起这里的,这些房子、花、树、车子,跟我们没有关系。我毕业后找到这个程序师的工作才两年,第一年的薪水一半用来还读硕士时问亲戚借的学费了,余下的钱我攒着准备买一部小跑车,那种叫银子弹的道奇跑车。红雨一直在餐馆打工包外卖。她的钱除了寄回湖北家里,其余的都存着,她想交学费读一个图书馆的学位,图书馆职员薪水不高,但是工作清闲,也没有那么多人来竞争,据说。开进好莱坞大道的时候,风景大变,更加热闹。这时晚上十一点了,下城的夜生活正式开始,沿路一溜儿站满流浪汉和野鸡,后面的人群是去夜店的华丽族,明星富翁奇装异服,鹤立鸡群。我把车窗摇上去合上,红雨一声不响地紧握方向盘,目不斜视,好像多看一眼路边这夜夜笙歌她会变成盐柱。路灯和酒吧的彩灯跳动着映在红雨的脸上,跟她苗族人特有的高颧骨和无辜的眼神很搭,曾经不止一次有洋人问过红雨是不是波利尼西亚人。车窗外的人行道越来越挤,各种肤色的大胸,胖瘦不一的腿,空洞发呆的眼睛。摇滚歌手穿着带破洞的恤衫、油腻腻的摩托夹克,长发披肩的音乐家瘦骨嶙峋,除了胸口挂一把吉他,跟要饭的流浪汉别无二致。他们都站在夜店门口,在守门的保安面前来回徘徊。一个穿皮夹克浑身金属环的家伙,骑在哈雷上,正在跟一个小姑娘还是小伙子讲价钱,夜色中美女或者美少年裸露着细长的咖啡色的腿,看不出区别。红雨打工的餐馆在唐人街,经常有这些做皮相生意的人来买外卖,看到她这个孕妇,小费还会给得很多,还会要求摸一下她的肚子,求好运气。“你真给他们摸过肚子?!”我很奇怪,她居然不害怕。“没有啦!但是他们见到我还是很高兴,这些老外多奇怪啊!见到孕妇又有什么可高兴的!我妈说的,见到孕妇和怀崽的母猪都得往地上吐吐沫,消灾……”红雨没有觉得她话里对自己有任何不尊重。她国内的家在恩施,红雨是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廖姓苗人,来美国之前她是中央民族学院苗文专业的留校青年教师,持商务签证来到美国。按理她的英文是过了国内大学六级考试的,但是,她连加油站的柴油和汽油都搞不清楚,坚持说diesel(柴油)不在六级英语词汇中。你听她说话经常分不清她在说美国还是说湖北,湖北恩施和洛杉矶银湖,如果不是特别说明,它们在红雨的话语中差别不大,除了对孕妇和母猪的态度不同。我第一次见到红雨的时候,是在老费的旧家的派对上。一群人中间,一个小姑娘眉清目秀,漆黑的长发梳成马尾巴,穿着国内裁缝做的改良式旗袍,斩钉截铁地说:“打光火药,但这家伙没死透,倒在地上抽抽,我就毫不犹豫给了一枪托,砸得脑浆子都出来。脑浆子你们见过吗?不是全白的,像米豆腐……”这个彪悍女就是红雨。“谁的脑子?”座中有人问了我想问的。红雨:“野猪的脑子,比人脑子大,我也见过人脑子……是炸山开路时石头崩出来砸的……我二大大的脑子,好小……”那时正好是一九九二年洛杉矶黑人暴乱后,好多韩国人买枪保卫自己的店,怕被再次抢劫。洛杉矶的华人社区也怕被抢,见面都在商量购买武器的事。大家都没有摸过枪,不知道底细。唯一用过武器的人是红雨,她不厌其烦地解释在恩施用火枪打野猪的事。你人脑子和猪脑子都看过,怎么还怕高速公路?这是我不止一次问红雨的话,她的回答都是“湖北没有那么宽的路,我一上高速看到六排车道就晕”。红雨在和我结婚前,上下班打工都是坐公交车。穿过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我们的车从好莱坞转向佛蒙特大街,我也松了一口气,这条大路一直开下去,没多远就能拐进银湖区,快到家了。酒精的后劲开始上头。跟花花世界的下城比,这条路上灯光暗多了,四周也没有太多的行人,我昏昏然觉得很放松,把车座放倒,小睡一会儿……一声巨响,小本田狠狠地往前踉跄一下,几乎像要飞起来,然后又重重地摔回到地上。我的身体像坐过山车,被惯性猛地抛到前车窗上,旋即又被身上捆的安全带给拉扯回来。我彻底醒了,扭头看红雨,她的头狠撞到方向盘上,右脸上狠磕了一下,已经红肿起来。她双目圆睁,脸色煞白,伸手拉我,说:“小刚你没事吧?没事吧?我还好,就是脸上磕疼……”红雨把车停下来。我摸摸脑门,把车座放回直立状态,说:“我没事的,车子撞哪了?红雨你还好吧,除了脸别的地方疼吗?出门走几步看看……”我们各自打开车门,起身出来,红雨除了脸上挂花,其他看着都还好,她一边走一边整理自己的连衣裙,脚步平稳,我松了一口气。我们转到车的后部查看,发现整个保险杠掉在地上,后备厢已经被撞得缩进车体里。我倒没有那么心疼小本田,反正这车也老得不行了,应该换新的了。我们低头查看损坏的车尾,并没有注意那辆撞我们的白色中型货车。只听见身后那辆货车引擎熄火,车前灯随之暗了,车门推开,几个人跳了出来。我和红雨光顾着察看彼此的伤,一抬头,我们周围已经围了几个人。其中一个高个儿穿着连帽运动衣,背着光,他的大半个脸都缩在连衣帽的阴影里,看不清他的脸。他转身吼:“别熄火啊!你妈的蠢啊!把车开着。”随即货车的大灯随着引擎启动的轰鸣声又亮了起来。他的骂声在夜里粗重刺耳,大灯照得像审讯。另外两个围上来的黑人好像很紧张,低头看着我们的脚底下。接着另一个人从车里钻出来,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屎屎屎屎屎”。等他来到我们面前,我见他头上顶着缠夹不清的金发,身上穿着无袖的篮球背心、阔短裤,上身和腿上露出的部分布满刺青,包括他拿枪的手,枪对着我们。他看到红雨隆起的肚子,有点吃惊,把手里的枪本能地朝我这边多晃晃。在货车的灯光下,黑洞洞的枪口好像电影特写。红雨尖叫起来。“别开枪,求求你们别开枪!求求你们!把车拿走!”她用英文说着,声音又高又尖,像是锉刀划在玻璃上。她的湖北口音的英语听在我耳朵里,一瞬间我觉得五脏六腑都在害怕。“把车钥匙给我们!你他妈的快点拿出车钥匙!”高个子呵斥着。红雨弯下腰把车钥匙往前抛在高个子脚前的地上,车灯光打在她赤裸的手臂上,特别白,地上几块碎玻璃闪着寒光,她颤声说:“车钥匙给你,拿去吧,我们没有钱。”“我来我来。”我听见自己说,说着往后裤兜里掏钱包,一切都是慢镜头,我有种缺氧的感觉,脑子蒙了。我平静地掏出钱包,把里面的钞票掏出来,伸直手臂递过去。高个子一把抓过我手里的票子,转身就往货车奔,其他两个跟在后面,我松了一口气。这时我注意到那黑洞洞的枪口还在对着我们,没有挪开的意思。金发的小个子的眼睛里闪着疯狂的光。车灯下,我注意到他头上的金发是一个假发套,鬓角上有黑色的发茬从假发下支棱出来,让他脸上的疯狂更加恐怖,好像不是真的。这时我突然清醒了,路上所有的嘈杂都蜂拥进我的耳膜,就听见高个子和金发仔的叫骂声,枪响,子弹在空气中擦肩而过的锐叫,货车上的人拼命踩油门试图发动车子、引擎的活塞挣扎几下熄火复又爆破启动的声音。在这一片嘈杂中我听到红雨在一旁啜泣,只有一两声,我用手臂罩住她的肩膀,往路边的高草中退过去,蹲下,努力在乱晃的车灯中把身体缩小。金发仔坐进我们的车里,手里还是拿着枪,另一手捏着车钥匙启动车。他离我们是这么近,他脸上的粉刺在汗水下清清楚楚。随后,汽车排气管里冲出的热浪扑面而来,热浪中满是汽车废气的味道。在汽车启动的同时,我拉着红雨转身撒腿狂奔,马路隔离带杂草里的刺划破我的腿,我们拼命跑着,跑进一条更黑的小巷,跑过已经打烊的小店。直到发现牵红雨的手已经空了,我才意识到把她弄丢了,复又跑回去找。她倒在不远的路边,在一辆路边停着的车旁,赤裸的双腿上血迹斑斑,连衣裙的下摆已经撕破,高跟凉鞋只剩下一只。我以为红雨被枪击中,等我抱她起来察看,发现血是从她两腿之间流下来的。她还有气,活着。警察叫来的医院的时候,医生已经听不到胎音了。医生给了红雨引产的药,我坐在走廊里的椅子上等,医生跟我说为防止子宫大出血,要尽快引产——红雨没有被枪击中,但胎盘出了问题。引产前妇产科医生听我结结巴巴地说了车被撞然后被抢劫的事,叹了一口气,问这是不是红雨第一次怀孕。医生安静地听完,说:“第一次怀孕可能会出现各种复杂情况,包括流产。晚上车祸和惊吓是一个因素,但不一定是流产的决定因素。”说完他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你们还年轻,以后还会有很多次机会。”我唯一的念头是红雨活下来,别出事。引产很顺利,医生问我要不要见一见胎儿,我迟疑了一下,医生见我害怕,他说胎儿很完整的,就是很小,做父母的最后见一次是一个了结,我于是同意了。我被带进一间单人房间,类似于会客室,有沙发,有咖啡桌,沿墙的柜子上放了咖啡机和一排整齐的茶叶盒子,但不知道为什么那间房间给我布景的感觉,一切都是临时的设置。我在房间中站了一会儿,前面有一个落地窗,窗帘里面透出光亮。我走过去拉开窗帘,才发现窗帘后面只有一张一米半见方的大照片,不是窗户,这个房间根本没有窗户。大照片后有灯光设置,外面装了落地窗帘。窗帘拉上以后隐隐透出来的光线像天光一样,其实是大照片背后的打光。我在那张大照片前看了一会儿,那是从洛杉矶天文馆方向拍的城市鸟瞰,洛杉矶天文馆是我跟红雨约会时喜欢去的地方,那处风景我非常熟悉,没想到在这里看到。这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招呼以后,护士长推着小推车进来,她从小车上抱起平绒毛巾包的胎儿,递给我,告诉我不需要着急,想待多久待多久,没有人会打搅。我从她手里接过小白布包,胎儿只有儿童足球那么大,皮肤呈蓝紫色,很光洁,皮肤还有弹性,不像皱巴巴的新生婴儿的脸,双目微合,表情很安详。他靠近眉心处的眼槽微微凹下去,像红雨,苗人长相,我一眼就认出,然后我就不害怕了。我慢慢打开绒布包,看到他的全身,是一个男孩儿。相关图书推荐点击图片即可购买??《离岸流》著者:凌岚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年6月亲身体验,椎心书写,华人留学生在美国的“迁异、失落、孤独、忧悯”:异乡漂泊、中年危机、移民二代对父母的反叛与认同……个人移民生活的悲欢与中国的世界梦交叠,腾讯·大家“年度作家”凌岚小说首度结集!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哈金盛赞其为“华文文学中一块绚烂的景地”,学者黄子平作序,文学评论家何平推荐!-END-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第次推送如需转载注明出处联系请私信后台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apitia.com/pptzl/7361.html
- 上一篇文章: 与作者一起旅行旅行小书推荐
- 下一篇文章: DHLUPS发布紧急通知多国停运附E